诗画早茶 • 滋味江南
老早,弄堂口的大饼油条摊头,生煎馒头,没有人嫌贬油烟气味。在那时,这是实实在在的人间烟火。那时的人,从来没有人想到过要用现在家家少不了的脱排油烟机。
那种油烟气味,在那时,多少是好日子的感觉,令人感到亲切。
我常常在弄堂里穿过,每个门牌号头里的灶披间,飘出来的油烟气味,是几家人家的小菜味道,互相融和,串味,知根知底。
山东人家,大葱气味;宁波人家,咸腥气味和臭哄哄的味道;无锡人家在煎糖醋带鱼和烧糖醋小排骨;
洋派人家,罗宋汤的洋葱气味和番茄酱香味调和;节俭人家,咸肉放得长远,“油耗”气重;殷实人家,烧红烧肉,用热气肉,有“肉夹气”……味道刺激出这个城市的包容性,各色人家,各色人等,各地口味,嗅觉丰盛。
春天里,炖“腌笃鲜”,时鲜的竹笋和咸肉鲜肉,调养有铜钿人家的滋润;冬天里,也是有铜钿人家,飘出来红枣赤豆汤的味道,滋阴补阳;
有“坐月子”的女人家,灶披间多是鸡汤和蹄膀汤的气味,便觉大补;也有煎中药的味道飘出来,古朴,是老派的,仿佛是老房子里的红木家什。
没有红木家什的人家,双职工,多子女,也有香味四溢的日子,是趁爷娘上班的时候,从家里偷出来的米、黄豆、玉米,去弄堂口爆炒米花。
孩子们成群结队地跑过去,地上是一溜竹篮头,里面是个小铁罐,盛着米,或玉米、年糕片、蚕豆、黄豆……
破旧的炉灶里,火焰随着风箱的啪嗒啪嗒声,哔哔剥剥的声音;爆米花的一只手摇着炸弹似生铁闷罐,一只手拉风箱,脸上是一道一道污黑的汗水,埋头想自己的心事。
然而,身子是很稳重的,谁也没注意到,他会留神生铁疙瘩上的一个压力表,到了某个时分,便用力支起生铁闷罐,随手拖过一个脏得不能再脏的破麻袋,将生铁闷罐口对着麻袋里面,以一个熟练的动作封牢,抄起一根铁管套住生铁闷罐的口盖,跟着是一声“炒米花——响啦!”
孩童四下散开,蜷缩在墙根底下,捂耳。一声爆响,是香喷喷的味道,让人的鼻子一阵紧忙,鼻翼都瘪进去了。
与煎油条的油烟一起升腾起来的,还有煎生煎馒头的味道,多了点鲜肉味;锅贴就不同,因为不放芝麻和葱,吊不出鲜肉味;煮豆浆的热气大,味道却是淡,清水光汤,大不如小菜场里的豆制品摊头,那豆制品的气味,总还有浓重的豆腥气。
黄昏时分,是茶叶蛋和炸油墩子、臭豆腐干的摊头。味道好闻,且有给人诚实的感觉,棕色和深黄色的颜色,近似黄昏;
春天的公交车站,一只茶叶蛋摊头边上,一堆蛋壳,茶叶蛋的香味,一天世界。我忘不了那茶叶蛋的香味,但没有一点与茶叶有关,吃到嘴里的时候,也似乎是一种失落,没了想象中的香味,这趣味,全然在于吃之前和剥蛋皮儿的当口,满怀的欲望。
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每年临近端午,上海的街头多会有烧煮粽子的清香。和气候和节气有关,这粽子的气味,就在暮春和初夏时分上市。这样一些时日,犹如一串粽子,使城市和当时最雅致的情趣联系在一起。如今到了这时节,那气味离开了,去了别处。
在上世纪八十年代,华山路常熟路口的静安宾馆面包房飘出了奶油烤面包的气息,这是上海第一家法式面包房,结束了上海只有蜡纸包装的“枕头面包”和“罗宋面包”的历史,让上海人见识了短棍、长棍,特别是“别司忌”,一种烤面包片,使“静宾面包房”成为一种品牌;到了跨世纪的2000年,那个暖冬,在南京路江宁路口“梅陇镇”,“哈根达斯”的奶油巧克力气味就显得时尚,年轻而热烈。
许多年以后,我总要在春天里回味“腌笃鲜”,感受着食欲与激情,是一个城市的生态。我从中感受到上海的气息,并回忆起某个春天的夜晚,我在一个上海女人身边,看她熨衣服,那熨斗往格子呢大衣上熨烫的时候,漂浮出白汽,雾一般升腾,散发出好闻的上海女人气息。
一份人家,小菜就放在架橱里。架橱曾经是上海人家必备的日常家什。它通常被放在厨房间。在没有独用厨房的时候,它就搁在门边的角落,靠近饭桌。开架橱的最多的人,是这家人家的主妇。
我的好婆与我家的架橱紧密联系在一起。好婆的称呼,本身就很有上海地方特点;祖母的一种叫法。好婆身上总是带着一股架橱的气味。她拉开架橱门的架势,仿佛魔术师变戏法,她把头探进去,总归会有一些吃食给带出来。
那里面不知道有多少货色。生的,熟的。一包金针菜、黑木耳,和一小块烤麸,红烧,放糖,就是一只菜,现在的饭店里叫“蜜汁烤麸”;一块榨菜,两只鸡蛋,就可以做一碗蛋花汤;莲心和几颗红枣,加上大西米,就是一顿待客的午后点心。架橱就是上海人家的生计。
我从架橱里闻到的,是豆瓣酱、甜面酱、辣火酱的味道。有许多时候,这里面并没有豆瓣酱、甜面酱、辣火酱之类。许多家常的味道串起来,杂合在一起,酱的味道,就这样形成了。
好婆就终日在架橱旁。她也会在架橱旁思想。凭借着早年我呼吸到的架橱气息,我会在心中,从我的栖息之处看见她。
描述她与架橱之间的关系,最令人留恋的是她的豆瓣酱、甜面酱、辣火酱;是一种小菜:豆腐干切丁,肉丁,花生米,豆瓣酱、甜火酱,与少许的辣火酱,做出一个上海人通称为“辣酱”的菜。这菜在饭店里叫“宫爆肉丁”,后来肉丁改善为鸡丁,味道是一样的。
好婆不时地用手指刮清饭碗里的酱,并且要把手指放在嘴里吮。她从来不许我这样做。这关系到吃相。但她可以。她的吃相就是要把所有的剩饭剩菜吃清爽。
冬瓜小排骨汤,是我能够通过我的描述,看到的好婆与架橱的另一个经典之作。烧汤,好婆表达了一个上海人的讲究,小排骨先用水煮,倒掉第一潽沸水,然后炖,一边手握汤勺,不断将汤水上的沫滗干净。隔壁人家小孩烧饭烧焦的气味传过来,让我觉得饿。好婆就站在炉边的雾气里,构成一个剪影。
夏天,疰夏,这样的清水光汤,保持着营养与口味。架橱清理后也变得空旷。小菜被端在饭桌上,用一个纱罩,将一家人的菜肴盖起来。新煮的百合绿豆汤连锅浸在凉水里。
好婆一旁坐定,摇着蒲扇,构成另一幅剪影。日子里依然保留着架橱的气味,犹如故事的开始,上海人家最朴实的妇人孩童吟诵的市井素材。他们的自然环境典型场景是:流汗,摇扇,窗前开放的夜来香,三星蚊香烟雾缭绕,喃喃低语,为小家碧玉增色的无线电收音机。
如今,好婆不在了。牛奶经常潽出来,在煤气灶上烧焦的味道,挥之不去。
难忘江南味道。深入骨髓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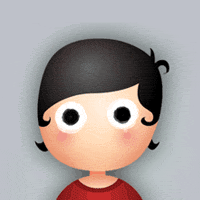
发表
26906人
签到看排名